科學頑童費曼

有一天,量子力學巨擘波耳主持一場研討會,與會者不乏諾貝爾獎等級的頂尖學者,會後他把擔任其助理的兒子叫到一旁,交代說:「記住坐在後面那個小夥子的名字,只有他不怕我。下次要討論什麼,先找他來;其他人都只會說:『是,波耳博士』。」這個小夥子就是才25歲的理查·費曼。

有一天,量子力學巨擘波耳主持一場研討會,與會者不乏諾貝爾獎等級的頂尖學者,會後他把擔任其助理的兒子叫到一旁,交代說:「記住坐在後面那個小夥子的名字,只有他不怕我。下次要討論什麼,先找他來;其他人都只會說:『是,波耳博士』。」這個小夥子就是才25歲的理查·費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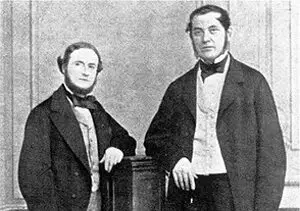
1859年夏日某一天,物理學家克希荷夫與化學家本生一如往常相偕散步。他們談起幾天前兩人好玩地用分光鏡觀測鄰鎮大火,竟從中辨認出鍶與鋇的特有光譜。
說著說著。克希荷夫突然停下腳步,瞄了一眼天上的太陽,轉頭對著本生說:「本生,我一定是瘋了!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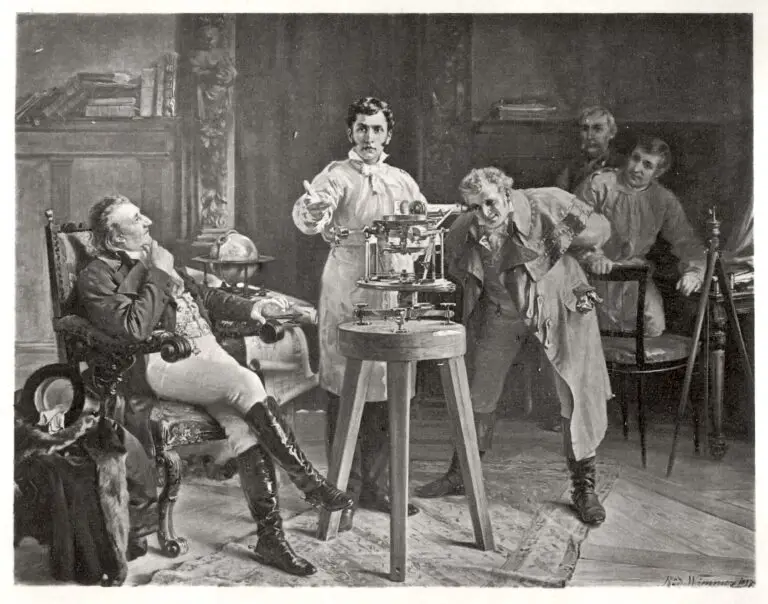
1801年七月裡的某一天,慕尼黑一棟房屋突然間轟的一聲棟倒塌了。14歲的玻璃工學徒夫朗和斐被埋在瓦礫堆下,大聲呼救。當瓦礫被挪開時,陽光照到夫朗和斐的眼睛,他不由舉起手來遮擋。他看著從指縫間穿過的光線,萬萬想不到他灰暗的人生自此也將被照亮,而且未來他還將會發現陽光中隱藏的秘密。

安培14歲時,爆發法國大革命,三年後,他的父親被送上斷頭台。父親在生活上與心靈上一直都是他的重要支柱,如今驟然橫死,讓安培難以承受而精神崩潰,如遊魂般晃蕩了將近兩年……。
安培猶如遊魂般晃蕩了將近兩年後,母親擔心其身體健康,只好將他送到偏遠小鎮休養,沒想到無心插柳,他就在那裡遇見未來的妻子。在愛情的滋養下,安培逐漸康復並覓得教職,兩人於1799年結婚,隔年回到故鄉里昂。
1800年,他們的第一個小孩在結婚週年誕生,政局也終於自十年狂暴混亂的法國大革命安定下來,展望未來,一切似乎充滿希望。安培不知道他將再度失去最愛的人。

1924年,愛因斯坦收到一封來自印度的信,信上寫著: 敬愛的大師, 我冒昧地寄上這篇論文,請您細讀並不吝指教。我很想知道您對這篇論文的看法。……我的德文能力不足以將它翻譯成德文,如果您覺得它還有價值,並能安排發表於物理學刊。……也許您還記得有個加爾各答來的人,請您允許把您的廣義相對論論文翻譯成英文,那就是在下。 您忠實的玻色 寫這封信的人是出生於1894年1月1日的玻色(Satyendra Nath Bose),30歲的他只是個遙遠東方的大學講師,在物理界仍默默無名。他冒然寫信要愛因斯坦這位大師幫忙,是因為他自認隨信附上的這篇論文是個重大發現,怎奈四處投稿卻都被拒絕,不得已才寫信求助於愛因斯坦。 說來好笑,這篇論文其實起因於他自己犯下幼稚的數學錯誤。 1921年,玻色在課堂上向學生介紹量子力學的起源,也就是黑體輻射的實驗結果始終無法用古典物理解釋,直到普朗克提出光量子的概念,才成功解決這個難題。他為學生演示古典統計力學的計算過程時,卻搞錯連國中生都知道的機率觀念。 同時擲兩枚硬幣會有四種結果:正正、正反、反正、反反,機率各是1/4,因此出現一正一反的機率是1/2,但他卻一時糊塗,誤以為機率是1/3。奇妙的是,最後竟然得出和量子力學同樣的結果! 玻色相信這絕不是巧合,他思考後提出「全同粒子」的嶄新觀念,認為光子是無法區別的,不像硬幣是獨立的不同硬幣,因此兩個光子是「正反」或「反正」也無法區分,應視為一種情況,因此機率是1/3,而非古典統計中的1/2。 玻色寫成論文投到許多期刊,但每個編輯都認為他的機率觀念有問題,他處處碰壁後,不得已只好寫信給愛因斯坦。 愛因斯坦果然與眾不同,一眼看出玻色觀點的重要性,不但親自把論文譯成德文投到《物理學刊》,還特定附上短箋為之背書。愛因斯坦在第二年也寫了一篇論文,將玻色的理論推廣到其它粒子,並預言了「愛因斯坦-玻色凝態」的全新相態(1995年獲得證實),而這種用於量子物理的統計便稱為「玻色-愛因斯坦統計」。 幸虧有愛因斯坦這樣的伯樂,玻色的理論才終於受到各界的重視,並且獲得廣泛的應用。玻色也隨即被擢升為教授,遺憾的是,直到他80歲過世前,始終未能獲得諾貝爾獎。為了紀念他,粒子物理標準模型中符合玻色-愛因斯坦的粒子(也就是負責傳遞作用力的粒子),都被稱為「玻色子」;如此,至少讓後人都無法忽略他對量子力學所作的貢獻。 補充一個軼事: 1927年,義大利政府為紀念伏打逝世一百週年,在科莫(Como)舉辦研討會,普朗克、愛因斯坦、薛丁格、狄拉克、波耳、海森堡、……等當代最著名的物理學家都參加了,玻色原本也在受邀之列,但是他卻沒有出席。 倒不是他有什麼私人因素不克前往,而是大會以為他還在加爾各答大學任教,於是在邀請函的收件人寫「給加爾各答大學的玻色教授」。但是玻色已經去了達卡大學,而加爾各答大學還有一位也姓玻色的教授,結果這位D. M. 玻色就代替好不容易出名的S. N. 玻色,參加了這場眾星雲集的物理大會。 不過D. M. 玻色比S. N. 玻色大8歲,分別在英國皇家科學學院與德國洪堡大學取得學士與博士學位,還曾進入卡文迪許實驗室學習。因此也有人認為他當時的學術聲望應不下於S. N. 玻色,或許邀請函本來就是給他的。 參考資料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