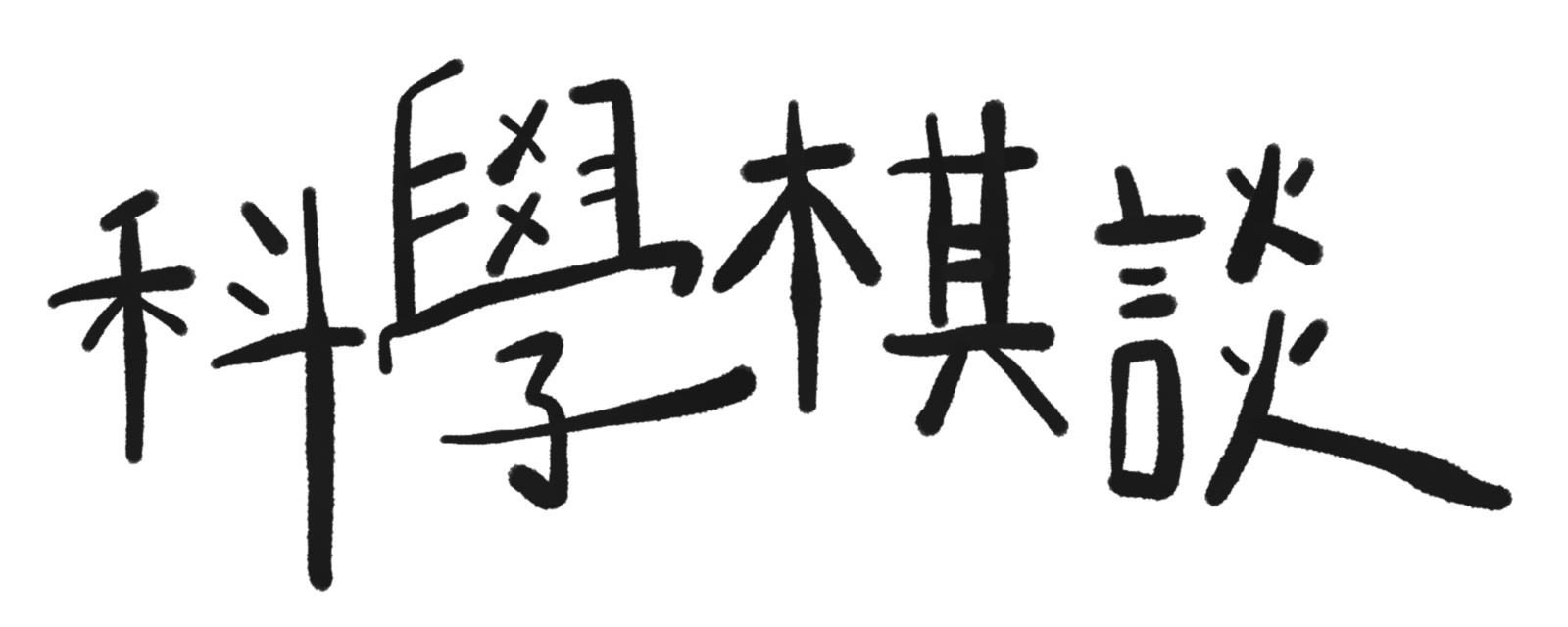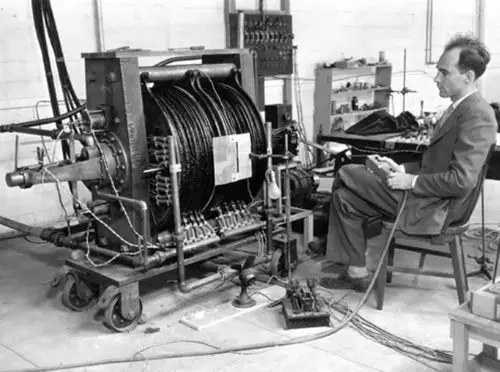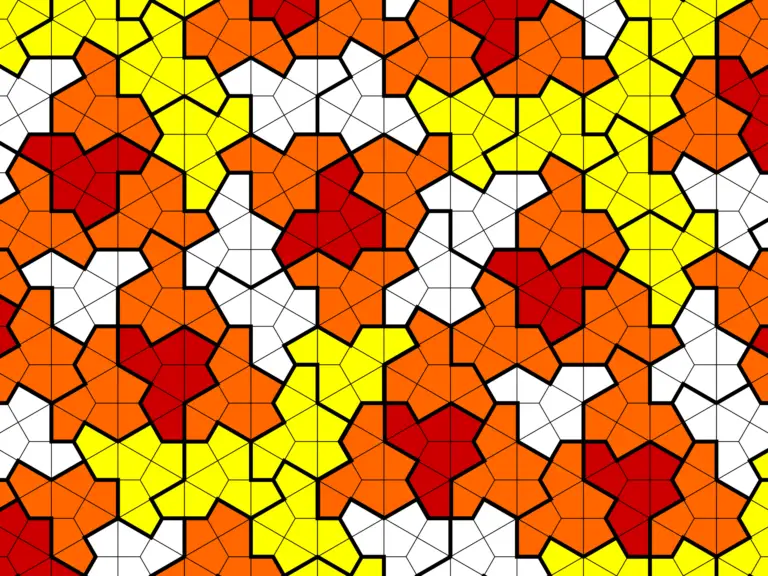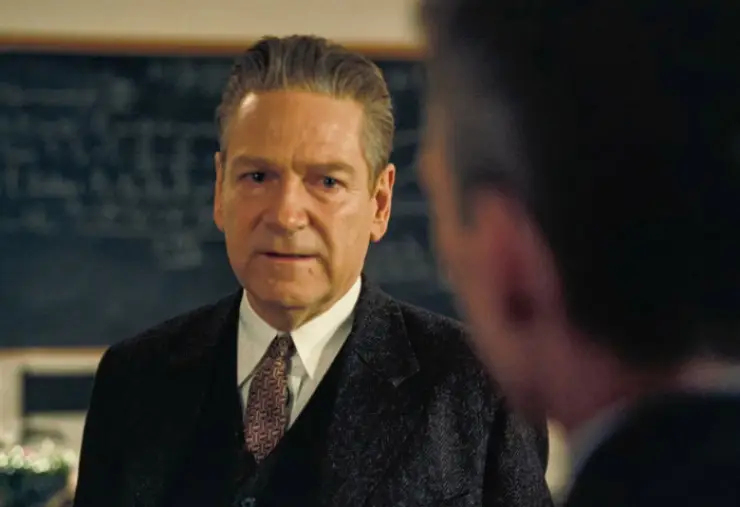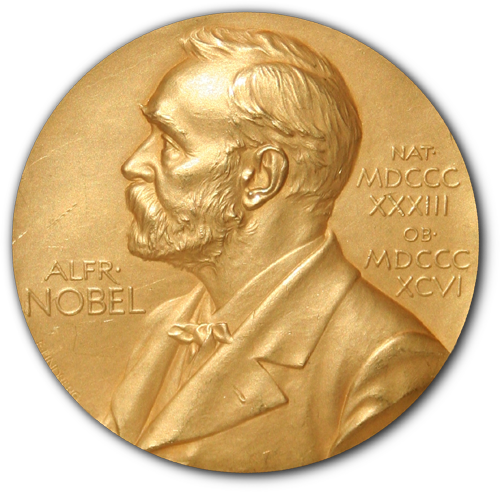開啟量子力學的人——普朗克
兩朵烏雲
1900 年,物理大師克耳文爵士 (Lord Kelvin) 宣稱物理學已臻完善,只要再花些時日解決「萬里晴空中的兩朵烏雲」即可。哪兩朵烏雲?一是邁克生-莫雷實驗 (Michelson–Morley experiment) 實驗顯示不同方向測得的光速都一樣,該如何解釋光在以太中的傳遞方式?第二朵烏雲則是還沒找到完全吻合黑體輻射實際數據的物理公式。
克耳文沒料到他眼中小小的烏雲竟很快發展成狂風暴雨,吹得物理學大廈搖搖欲墜。幸好愛因斯坦拂去第一朵烏雲,他以狹義相對論指出以太並不存在,鞏固了古典物理學。但第二朵烏雲卻變成巨大的龍捲風,來勢洶洶的量子力學將古典物理學連根拔起,而最初拍動翅膀引發颶風的,正是這篇要介紹的普朗克 (Max Planck, 1858-1947)。
其實普朗克進入大學時,一位物理學教授也曾告誡他說:「這門科學中的一切都已經被研究了,只有一些不重要的空白需要被填補」,勸他不要選讀物理。幸好他沒聽勸,後來才會鑽研難倒所有物理學家的黑體輻射問題,因而開啟了量子力學。
黑體輻射
什麼是黑體輻射?我們知道鐵塊加熱後,隨著溫度提高,會逐漸從黃紅色轉為藍白色,代表頻率也越來越高,輻射能量也越來越強。不過物體除了本身的輻射,也會反射外來的光和熱,若想研究輻射強度與溫度的關係,就要設想一種理想物體,能完全吸收外來的電磁波,不會反射出去,如此輻射強度就只取決於它本身的溫度;而不會反射代表是純然黑色,這種物體就稱為黑體。
現實中當然不存在真正的黑體,不過卻有相當類似的東西:鋼鐵廠的煉鋼爐。煉鋼爐有個小洞,從洞口測到的輻射強度與波長,便是爐內散發的輻射,幾乎沒有外來的影響。
其實鍊鋼正是科學家研究黑體輻射的起因。19世紀中葉開始,鋼鐵工業隨著煉鋼技術的突破快速成長,各國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。到了19世紀末,英國已被德國超越,但不久美國又追了上來。德國物理學家維因 (Wilhelm Wien) 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,便蒐集煉鋼爐的輻射數據進行研究。
他先於1893年歸納出「維因位移定律」,指出不同溫度的黑體,其輻射強度在哪個波長達到頂峰。接著他以空腔模型模擬煉鋼爐,根據熱力學於1896 年推導出特定溫度下,黑體輻射強度與波長關係式的「維恩分佈定律」。不過這條公式只有波長較低的區段符合實際數據,波長較大(也就是低頻)就有不小差距。

英國物理學家瑞利 (3rd Baron Rayleigh) 則於1900年,從電磁學的角度歸納出輻射強度與波長四次方成反比的公式,便可符合黑體輻射在波長較大的區段。但根據能量均分定理,空腔內的電磁波會分布於不同波長,包括紫外線、γ 射線以上極短的波長。這顯然並不合理,怎麼可能隨便加熱一個物體,就會產生趨向無限大的能量?
於是瑞利在公式中加進針對高頻的限制,但這麼做其實沒什麼根據。英國物理學家金斯爵士 (Sir James Jeans) 於1905年提出更完整的推導,將它修正為「瑞利─金斯定律」,但這條公式仍無法吻合高頻區段的實際數據。
量子假說
在維因和瑞利分別提出黑體輻射的定律之際,普朗克也已經研究這個問題一段期間了。
其實普朗克剛進大學時,一位物理學教授曾告誡他:「這門科學中的一切都已經被研究了,只有一些不重要的空白需要被填補」,勸他不要選讀物理。但他回答說:「我並不期望發現新大陸,只希望理解已經存在的物理學基礎,或許能將其加深。」還是選擇了物理學。
1879年,普朗克以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研究取得博士學位,隨後在不同大學任教。1894年,他開始注意黑體輻射的問題。經過多年嘗試,普朗克最後發現若是放棄「能量的變化是連續的」這個傳統認知,也就是假設能量像粒子般具有最小不可分割的基本單位,便能得出與實驗數據吻合的黑體輻射定律。
1900年底,普朗克發表「普朗克定律」,在公式中加入「普朗克常數」h(大約是 6.626 x 10⁻³⁴ 焦耳·秒,若以電子伏特取代焦耳,則是 4.14 x 10⁻¹⁵,所以世界量子日才訂為4月14日),如此一來,黑體輻射的所有頻段的實際數據都能吻合。

不過普朗克並未意識到自己揭開了量子革命的序幕,他只把量子的概念當作是求取公式的技巧,並不具物理上的實質意義;學界也普遍持同樣看法。
但1905年愛因斯坦在解釋光電效應的論文中,主張每個光子的能量E,等於其頻率ν乘以普朗克常數h,也就是光子的能量是有基本單位的,量子才成為實實在在的物理概念:光量子。
不過大家對於光量子仍半信半疑,直到十年之後密立根以實驗證實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理論,此外波耳的原子模型也是奠基於此,量子力學才逐漸獲得認同,普朗克也於1918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(愛因斯坦、波耳、密立根則分別於1921年、1922年、1923年獲獎)。
雖然身為量子物理的開創者之一,但普朗克和愛因斯坦一樣,無法接受愈來愈脫離古典因果論的量子理論,一直試圖將量子現象納入古典物理中,卻始終徒勞無功。他晚年便感嘆道:「長年的曠日廢時只是徒勞,被大部分同仁當成悲劇看待。」
政治動盪
其實在獲得殊榮之前,普朗克在德國物理學界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他於1912年榮膺普魯士科學院輪值主席之一,擔任柏林大學院長時,又成功說服愛因斯坦回德國任教。
不過就在他滿腔熱血致力於提升德國學術水準之際,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,戰後德國在《凡爾賽合約》的懲罰下,經濟蕭條、政治動盪。普朗克一心想復興德國的科學地位,努力爭取國外經費,讓科學家能安心做研究。孰料納粹崛起後,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。
普朗克於1930年接任威廉皇帝學會主席。三年後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,隨即頒布公務員法,禁止猶太人在大學與研究機構任職。時任威廉皇帝學會化學所所長的哈柏雖是猶太裔,但因對國家有巨大貢獻,彷彿有免死金牌,然而他仍辭職並離開德國以示抗議。相較之下,普朗克勸說希特勒無效後,未再有進一步動作,坐視猶太同仁被迫流亡,不免讓人質疑他的節操。
但對普朗克而言,並非他戀棧權位,而是擔心倘若讓納粹主義者接任,只會造成更大傷害;他留在現職,還能盡量照顧受到波及的同仁。事實上,當哈柏在1934年客死異鄉,普朗克便甘冒大不諱,為他舉辦悼念會。另外他在1936年卸任前,也設法讓一些猶太裔科學家繼續在所內工作。
延伸閱讀:〈你愛國但國家不愛你——哈柏的悲劇人生〉
家破人亡
普朗克卸任後已近八十歲,但仍四處演講,支撐他的,就是復興德國科學的使命。不過他卻不斷遭受打擊。
他的大兒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死於戰場,兩個女兒也隨後相繼因難產而亡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盟軍轟炸柏林,他的住家全毀,所有藏書與研究筆記也付之一炬。二兒子又於1944年參與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被捕,普朗克寫信向希特勒求情未果,眼睜睜看著兒子第二年被處死。
大戰結束後,為了表揚他的貢獻,威廉皇帝學會於1946年更名為「馬克斯·普朗克學會」,並給予他名譽主席的榮銜。但隔年普朗克即因病過世,享年89歲。
很難想像普朗克如何面對一直不如意的人生:歷經兩次國家戰敗的屈辱、兒女先後死於非命,就連他掀起的物理革命——量子力學,也不是他想要的。無論如何,他的貢獻與付出有目共睹,二次大戰結束後,威廉皇帝學會於 1946 年更名為「馬克斯.普朗克學會」,並給予他名譽主席的榮銜。但隔年普朗克即因病過世,享年89歲。
如今馬克斯.普朗克學會轄下已有超過 80 個研究院,涵蓋各種領域,普朗克在天之靈應該能感到欣慰。這些研究所大多座落於德國各個城市,我到慕尼黑特地去拍照留念的馬克斯·普朗克物理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。對我而言,普朗克一生研究的正是物理,因此這個研究所別具意義。

參考資料:《為第三帝國服務》,Philip Ball 著,張毓如 譯,麥田出版